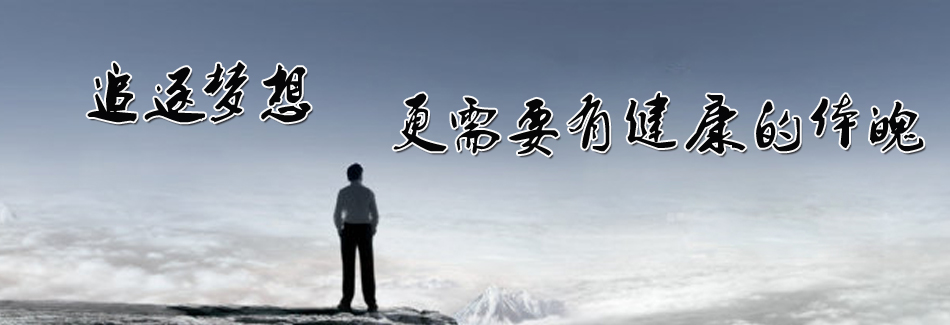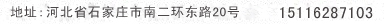愿ldquo她们rdquo被这世
闲篇儿
主播
张钰良出品
惟物论FM
扫码添加小张同学拉你入群
我们群里见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书,是阎连科的《她们》。这是一本散文,书写了阎连科家里许多女性的故事。
阎连科老家在河南嵩县,从小生活在农村。所以在写到书里女性的时候,其实差不多也都在写农村里的故事。阎连科所经历的二三十年前的农村,那个环境下的女性,她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
阎连科作品《她们》
我们今天一说女性话题,大部分说的都是都市女性,因为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高了,所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城市。但是阎连科书里写的农村女性,也代表着一个时代。
1
阎连科早年在部队工作,他抱定了主意,死活也不想在农村过一辈子,就想当个城里人,所以在部队的时候,他训练和工作都很玩儿命。对阎连科来说,当时能够走出农村唯一的机会,就是在部队提干。当了干部,城里人的身份也就解决了。
可是当了三年兵之后,军队里面的政策变了。普通战士不能提干了,想提干只能考军校,可是考试的条件还特别严,必须是党员,必须是班长或副班长,而且年龄不能超过20岁。这三条缺一不可。面对这么严苛的条件,阎连科肯定满足不了,所以提干这条路是没戏了。
年刚入伍时的阎连科(右)
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一转眼,到了该退伍的日子了,部队留不下了,他就跟别的战友一起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但就在火车马上要开动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部队的团长坐着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站台上。他从车上下来,又上了火车,满车厢的喊:阎连科在哪儿?
阎连科听见团长喊自己名字,赶紧站了起来。这时候团长说,你可以提干了,赶紧拿着行李,跟我下车。
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阎连科没听明白,结果一问才知道,他之前跟战友一起参加了全军的话剧演出,他们演的这个话剧不仅拿了奖,还被军区领导点名表扬,所以特批了一些提干名额。阎连科刚好是这部话剧的创作者,所以就能跟着提干了。
面对这么个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机会,阎连科反倒犹豫了。因为当时中国和越南正在打仗,他担心部队把他派到前线去。所以他跟团长说,我能不能先回家,跟家里商量一下?团长说,给你七天时间,如果第七天我没看见你人,那我就把提干指标给退回去了。
阎连科带着纠结的心情回了家,没想到家里人不愿意让他提干。因为在当时,他大哥在外地工作,两个姐姐都嫁人了,他爸爸还有很严重的哮喘病,家里指望他能回来种地。这可把阎连科郁闷坏了。
面对这个情况,一家人僵在那了,谁都没个主意。最后还是阎连科的大哥站出来跟家里人说,让他走吧,家里多大困难都有我呢。就因为大哥这一句话,阎连科的命运算是彻底改变了。
提干这件事尘埃落定,接下来的一件事,就是家里要给他张罗对象了。因为那时候的阎连科已经23岁了,这岁数在农村可是绝对的大龄青年,所以家里恨不得赶紧帮他把婚姻大事定下来。
提干后的阎连科
图片出处:南方人物周刊
后来有个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而且领着这个姑娘去了他们家。到了家之后,这姑娘表现得挺贤惠,帮忙做菜做饭,打扫卫生,一个劲的干活。媒人对阎连科说,怎么样?不错吧?你们家就缺这样一个人。看到这些情况,阎连科觉得自己已经躲无可躲,退无可退了。
但是这时候,阎连科的二姐问他说,你同意这门亲事了?二姐这么一问,阎连科还真有点儿懵,不知道该说什么。紧接着,二姐又跟他说,你要是不同意,就赶紧说不同意,晚了可就没机会说了。但是阎连科在书里说,他当时说不出不同意,就好像他这一辈子也从来没有正式对谁说过我爱你。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性,非常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含蓄除了不好意思表达对一个人的好感,在相反的层面,也往往不善于拒绝别人。所以阎连科最后没说什么,家里也认为他同意了。他的妈妈给了那姑娘家里块钱,算是订婚的彩礼。从此往后,阎连科就算是有对象的人了。
80年代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
元人民币是个不小的彩礼了
相亲这件事定下来了,阎连科也该回部队了。因为团长就给了他七天时间,所以他要赶着日子回去,等着提干。回去之后,部队告诉他,提干之前要做个培训,让他去《战斗文艺》杂志的编辑部学习一段时间。
到了这个编辑部,阎连科发现工作还挺轻松,每天无非就是接电话,取信,读作者的来稿。在这期间,他时不时地要和对象写信,而那个姑娘也给他回信,两人就这样联系。
有一次,军队里的一个文化部长抱着闺女找到阎连科,跟他说了说培训和学习的事情。这些事都说完了,军队领导特别抱歉地拿出一封信给了阎连科。这信是阎连科在农村老家的对象给他寄过来的。信寄到了编辑部,同事收到信之后还以为是普通的读者来信,便拆开了。拆开之后发现弄错了,所以领导赶紧过来表达歉意。信的内容大家都没看,不过拆信封的时候从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大家看了照片,都说这姑娘长得不错,看来阎连科找了个好对象。
军队领导解释完了,刚要走,忽然又站住,小心谨慎地问阎连科,你对象什么文化程度啊?
阎连科一听这问题,赶紧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跟领导说,小学吧。
本来阎连科以为领导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领导走到门口,抱着闺女跟他说,我觉得这批文化骨干里,你最有可能成为作家。我也是农村当兵进城的,提干之后才找对象成了家。其实提干之后在农村找对象也没什么,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跟她吹了,可千万别让他告到部队里面来。我是为你好。领导说这话的时候吞吞吐吐,说完之后转身走了。剩下阎连科一个人,开始想这件事。
阎连科最后给那位姑娘写了分手信
凭良心说,阎连科算不上喜欢这个姑娘,但是因为自己不会拒绝别人,让大家以为他很乐意,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现如今都订婚了,还能不能再反悔呢?他想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只能用伤害一个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
最后他给那个姑娘写了信,用了一千个一万个对不起要跟人家分手。很快,他也收到了那姑娘的回信。姑娘不太会写字,只能找人代笔写。但是这回信里面,姑娘历数了种种自己对阎连科他们家的好,说阎连科是陈世美。不过这姑娘也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告到你部队去,我知道,我这一告你就完了,你就得跟我一样回农村种地了。我只怪我没有好好读书,我怪我命不好,只怪我们都是农民,都想过上好日子。
2
80年代的农村女性想要离开这片黄土地太难了。当时的人口不能随便流动,人一定要跟户口牢牢绑定在一起,而且户口还被严格的分成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想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就算有这种机会,很大程度上,这种好事也落不到农村女性的头上。
假如考上了大学,可以把户口迁到学校。毕业了分配工作,有很大机会就留在城里了。但这是大学的情况。如果我们倒着往回看,就会发现,农村家庭在过去有好多女生念书念到一半,家里就不让去了。他们得把钱留下来,让哥哥或者弟弟去。姑娘家差不多能识字就行了,后面结婚生孩子,种地干活儿。既然生在了农村,这也就是你的命。当时没有多少人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去帮助一个农村姑娘改变命运。哪怕她们自己再怎么想离开农村也是徒劳的,家里的主观因素和时代的客观因素,都不允许她们这样做。
农村家庭经常牺牲女孩读书的机会来培养男孩剩下唯一一条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的路,其实走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很多人在婚姻面前都很现实,咱们中国历来就讲究门当户对。一个城里小伙子,就算喜欢上一个农村姑娘,家里也八成会不同意。当然了,这事如果反过来也是一样,城里的姑娘照样看不上农村的小伙子。阎连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相亲经历,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洛阳市的女军官,他觉得人家不错,可是人家看不上他。但是若干年之后,当这个城里的姑娘在报纸上看见了阎连科写的文章,就开始后悔了,并且埋怨当时的介绍人,说你怎么早不跟我说他会写文章呢?但这时候后悔也晚了。
阎连科和那个姑娘分手之后,又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的太太,两个人结了婚。他太太是开封人,是城里人。结完婚,他们有了孩子。当孩子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阎连科一家三口回老家。走在村子半路的时候,从对面走过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就是以前和他订过婚的姑娘。但是这会儿的姑娘,可不是从前的姑娘了,她也有孩子了。她在路上走着,左右两边连大带小跟着三个小姑娘,拽着她的衣服。她怀里还抱着一个更小的小女孩。而且这个时候,她又怀孕了。这些孩子里面没有男孩,而重男轻女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农村,甚至于在今天的某些地方仍然盛行。
生育观念的改变不是一两句口号能带来的
通过阎连科的故事,大家应该就能体会到80年代中国农村女性的一个缩影。不要觉得这样的故事距离今天的我们很遥远,我相信在今天的某些地方,类似的故事仍然在发生,只不过它和过去相比,范围缩小了很多倍,而且可能换了一种形式。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对女性的要求都很传统。当我们想要赞美某一个女性,经常会说这姑娘特别贤惠,在家相夫教子,是个贤妻良母。这应该是对一位女性很不错的评价了。但是我前些天看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关于这方面话题的一些观点,是我非常认同的。
这本书是吕思勉写的《中国通史》。他在写婚姻这一篇文章的最后说道: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让女子回到家庭去,这种口号只有开倒车的人才会去高呼。好多人都说女学生变坏了,不如旧式的传统女性,因为家务活都不会干。但这些女性正是因为疏远了家务,参与了社会的工作,才让自私自利的组织逐渐破坏,公平博爱的组织逐渐形成。贤妻良母,不过只是贤奴良隶。我们该教一切男女天下为公的志愿。
吕思勉所著的《中国通史》
这是吕思勉在年写的书,但是思想已经非常进步了。我特别认同他的观点。女性不应该只为了家庭而存在,每一位女性都应该有选择并且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尤其在今天,我们很多的政策相比与过去已经非常开放了,所以我觉得就家庭的层面来说,不应该再给女性从主观上制造更多的难题。当代女性,不管是生活在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她们不应该和家庭,和土地绑在一起,她们更不是生育的工具。女性应该去追求独立,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这个世界,而这个社会也应该给予女性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她们值得,也应该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
3
在《她们》这本书里,除了相亲的故事,阎连科还写了家里很多位女性。但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他的母亲。
阎连科在书里面写过关于母亲的一件事。他母亲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媒人,经常帮助村子里面的年轻人张罗相亲。按说这是个好事,但是这里面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它还真有些门道。
有一次,阎连科的母亲给村子里的一家人安排相亲。这家人的孩子是个小伙子,想从邻村找一个姑娘。但是小伙子他们家很穷,家徒四壁,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以这种条件相亲,实话实说,不太可能有姑娘愿意嫁过来。所以为了让这个小伙子相亲成功,有人出了个主意,让他从别人家里拉来点儿家具过来充充门面。但是阎连科他母亲不太同意这么做。因为借来家具装了样子,人家姑娘一看这条件不错,嫁过来了。可是嫁过来之后怎么办呢?这日子是这么好过的吗?这不是骗人家姑娘吗?所以阎连科母亲不太愿意这样做。但是最后,她还是磨不开村里人的面子,只能同意这样帮着人家去说媒。
80年代农村家庭的陈设
在阎连科母亲答应了这事之后,小伙子家里就开始准备了,弄了一屋子还不错的家具,还摆上了毛主席像,家里弄得有模有样。等阎连科母亲把邻村姑娘领来了,人家姑娘一看,还挺满意,然后两家人便开始商量后面的婚事。
可是这事过去之后,阎连科母亲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自己欺骗了姑娘。所以她打算把实际情况告诉姑娘,哪怕把村里那家人得罪了,也不能毁了姑娘一辈子。但是当她把实话跟这姑娘说了之后,没想到姑娘却说,您以为我看不出来他们家的家具都是新借来的呀?打扫的痕迹这么明显,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现在咱这村里相亲不都是这样吗?您之前上我们家去,没发现我们家的家具也都是借来的吗?
姑娘这么一说,让这件事变得非常有戏剧性。而在戏剧性之外,它也反映出80年代农村男女在相亲时候的一种状况。而且同样是说母亲善良,阎连科的表达方式很不一样。
春晚上的小品《相亲》反映了当时实际的情况
在书里,还有一个故事也让我印象特别深。阎连科后来在北京定居了,他母亲上了年纪,搬到了北京跟他一起生活。有一次她母亲洗澡,一个人坐在浴室里面,洗得非常慢。那时候母亲已经八十岁了,腿脚不怎么灵便。
洗得时间长了,家里人不太放心。阎连科的太太去到浴室门口跟他母亲说,要不我帮您搓搓背吧。母亲却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洗就行。又过了一会儿,还不见老太太出来,阎连科的儿媳妇又过去了,说奶奶,我帮您搓搓背吧。但老太太还是说不用。最后老太太在浴室里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大家都不太放心,最后阎连科就过去了,从门缝那里问他母亲,说要不我帮您搓搓背吧。这时候他母亲说,那你就进来帮我搓搓吧。
按道理说,儿子帮母亲搓澡,这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当时他母亲只穿着一件贴身的短裤,再没有其他的衣服,这种状态跟裸体也差不太多,并不是太方便。可正是这种不方便,让阎连科终于意识到,自己母亲的身体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她头发白了,有着双下巴,身上有脂肪瘤,全身的皮肤也全都松弛的垂下来,就像阎连科在书里说的,一个女人的生命史,都体现在她身上。甚至连她母亲自己都说,好丑啊。
前两天,我在知乎上看见一个问题,有一个美女妈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好多朋友都在回复里面把自己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晒出来,样子都很好看。但是愿意把妈妈老了之后的照片也晒出来的人,却没有那么多。
衰老在她们身上留下了痕迹,谁也抹不去
一个人的身体是不会骗人的,60岁的人再怎么锻炼,身体也一定和20岁的年轻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美好的身体,但是我们好像很少意识到,因为衰老而导致的身体的变化,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知乎上那个问题的回答里面,所有的妈妈都年轻,都漂亮,但是妈妈总有变老的那一天。而一个女性这一生当中所发生的的一切经历,也都像日记一样,在她们的身上留下了痕迹,谁也抹不去。
在这本书的最后,阎连科写完了家里的女性,还写了几个他听说过或是采访过的女性。这些女性的命运大多很悲剧,有的坐牢了,有的被人杀了,都很悲惨。但是这些悲惨故事的背后,表现的是常人不太会去
- 上一篇文章: 警惕毁掉女性胸部的十大杀手
- 下一篇文章: 第期清体营全程集锦